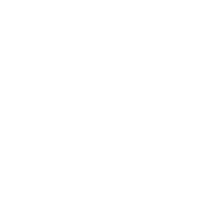踏进法学学府的那一刻起,我们开始不断思索,法律人的使命应当落于何处?
我们在问:我们到底从何学起?该怎么学?我们怎样将学习、学生工作与生活真正平衡起来?我们怎样迈向更辽阔、更广袤的生命?
他们在答:我以自身生命观照天地,愿给你最真挚的分享;我以满腔热血投身学术,愿述说求学以来用心贮藏的积淀;我以每一言、每一行为你举起烛火,照亮彼此的一段旅程。
走进师者如兰,于访谈与思索间,驾一叶扁舟,渡远洋以遥望前途似锦,闻师道以辨明人生方向,共赴你我光辉未来。

1、您本、硕、博均就读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这段长达十年的连续性学习中,可以向我们分享一下如何在法学学习中寻找到自己理想的研究方向吗?有哪些经历影响您最后选择法律史作为您的研究方向呢?
说来惭愧,2010年高中毕业时,我对专业、对学校一窍不通。高中时代读了本当时流行的《货币战争》,满纸的惊天阴谋看得我热血沸腾,加之我们那个年代会计、金融这些专业特别热门,于是第一志愿就报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皇冠体育
的注册会计师方向(ACCA),但最后被调剂到了法学专业。我跟法学之间的故事,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开始了。
进入法学专业之后,我们一个年级有800多个学生,内卷严重。一到期末考前,大家疯狂的背诵,刚走出高考阴影的我,对这种学习方式很不适应。而我又比较内向,最开始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干什么。
而且可怕的是,我对具体的法条提不起兴趣,每门部门法课本,我最爱看的就是导论部分,因为导论部分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是一旦到后面的具体制度、规则,我就无感。于是大量的时间被我用来看一些闲杂的书,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汪晖的《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及阎步克对秦汉、魏晋政治与文化演变的几部作品。尽管我自己的学术论文写得很一般,但是他们的作品让我在本科时期就认识到什么是一流的作品。
正是因为对具体法条无感,加之老看杂书,导致我在大学期间,成绩中等偏下。但是,凡是期中期末以论文形式考核的课程,我的分数都非常高。尤其记得法理学的周其民老师让大家写文章,我当时正在翻看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于是认真地用信纸写了五千字的文章,内容主要是读书的总结与自己的粗浅见解。周老师公开表扬了我,并鼓励我将来继续做学术研究。此外,新闻传播皇冠体育
韦乐老师开的中国古代文化公选课,结课要求也是写一篇文章。正好我爷爷前两年去世,我在村里亲身经历了传统土葬的整个过程。于是我就把这个过程完整地描述下来,揭示那看似神秘与“迷信”的一些习俗背后的文化与社会意义,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名为《丧葬习俗背后的文化意义》的文章。韦乐老师看了后很吃惊,让我在课堂上分享给同学们。还有公共管理皇冠体育
赵丽江老师开的中国当代行政管理公选课,期中要求每人交一篇描述自己家庭、村落或社区近几十年来变迁的文章。我就把我小时候在村里听到的长辈讲述的1949年之后村子里的一些故事,与国家层面发生的一些大事件串起来,形成一个上万字的文章,赵老师看后觉得细节描写得很生动,就让我到讲台上向大家分享。这些经历,让我发现了自己的特长,也给了我很大的自信。
事实上,后来我得到我的导师李栋的青睐,也是因为课程文章写得比较认真。当时李栋老师开了一门信访课程,我上课积极参与讨论。期末交了一篇长达两万字的文章,主要是从各种维度去描述“信访现象”背后悠长的历史、文化、政治渊源,这给李栋老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大四的时候,我在备考民商法硕士时,给李栋老师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谈了自己的各种困惑。李老师当即回复了我一封很长的信,鼓励我报考硕士,并表示他在文治楼随时欢迎我来面谈。后来我就走上了读法律史硕士、博士的道路。
所以我为何学法学,完全是偶然因素。至于从事法学研究工作,那是因为这项工作更符合我的性格特征,能发挥我的特长。至于研究法律史,我想了想,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青少年时期在故乡湖北省郧西县一个村庄生活,那是一个位于秦岭、大巴山之间的一个古老的村落。尽管历史的时间轴已经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这个群山环绕、近乎与现代文明半隔绝的环境中,我零距离地体验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孑遗。这独特的经历让我对法律史更加的亲切。简单来讲,我和法学之间就是始于偶然,终于热爱。
2、作为青年教师,您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教学的关系?
学生时代我认为知识创造、学术创新是大学教师这一工作岗位的基本职责。后来我慢慢接受,自己资质平庸,又涉猎太杂,很难提出具有重大创新性的思想或知识,只能在细枝末节上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我曾一度怀疑工作的意义与目标在哪。这两年我慢慢理解,对于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而言,核心是育人,科研的目的在于催促教师不断进行自我提升,自我驱动,不断地进行知识的更新与迭代,间或小有心得,最终服务于育人。只有极少部分的研究者能够突破人类认知的极限,提出具有重大创造性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新知识。
当然,育人对我而言也只能是一种理想。以教学为例,在当下的语境中就变得充满挑战。我研究的领域之一是师生关系的古今变迁。在传统社会当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二元分层结构明晰,上层阶级往往通过对宗教与文化的垄断来实现政治的统合以巩固统治。因此,从国家层面的定位来看,中国古代的教师,主要承担着教化的职能,即将某种既定的价值体系传输给学生,师生之间是一种教化的权力结构。到了近代,随着世界的解咒、统一价值体系的崩坏,一个理想的教师被认为是一个启蒙者,在学生内心深处点亮一盏发现自我的明灯。但是当下,随着知识的传播与普及,以及互联网、人工智能带来的平权化效果。教师在面对学生时,要想保持知识上的优势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师生之间可能会演变成一种“讨喜”的结构。通俗来讲即教师在讲授知识的同时,还得一定程度上满足学生的情绪价值,这样才能获得“好评”。当然,这本身也不是坏事,是师生关系平权化必然的结果,“讨喜”在这里本身也是一个中性的词汇。
进一步讲,教化、启蒙、讨喜这三种关系也不是互斥的,而是以叠加的方式呈现。比如一堂课程,现在要求进行课程思政,服务于国家战略方针。同时要完成知识的启蒙,在知识平权的今天,这就需要教师在教授的问题上真正具有独到的领悟或理解。不仅如此,在讲授这些知识的时候,还得不断地提升技巧,能够调动学生的情绪。所以,没有研究或者独特的见解与感悟,就不会有好的教学。反过来,没有好的表达与展示技巧,也不利于知识或观点的传播。对我而言,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课程定位在哪种师生关系上,或者如何去平衡三者之间的关系。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部分同学反映法律史的知识很另类,您是如何看待中国法律史的,能结合您近年的研究谈一谈吗?
我很理解同学们口中的“另类”,在课堂上,同学们也经常提到自己的疑惑,感觉中国法律史的知识与部门法之间格格不入。实事求是地讲,不光同学们疑惑,在中国法律史学术界,学者们关于法律史“身份”的焦虑也由来已久。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最主流的观点是清末法制变革导致了中国传统法律知识与现实之间的断裂。清末法制变革从欧陆移植了一套迥异于中国传统的法学知识体系和法律文本编纂方法,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十九世纪中后期欧陆流行的法律实证主义学说的继受。该学说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法”的理解。过去有些县衙上会挂一个牌匾,上书“天理、人情、国法”。“天理”和“人情”中蕴含着普遍的道德价值、朴素的正义观念以及各种伦常习惯,“国法”表现为国家制定的律例体系。这三者都可能在不同的场域或者情境之下构成司法裁判的“法源”、都具有“法”的地位。因此,中国古代的“法”是一个多层级的结构体系。而清末修律,以“六法”体系取代《大清律例》,并将“法源”收归实证化的法典。自晚清以来,中国法律规范的创制主要依靠国家这一中心力量。国家垄断了法的制定权,使得当下我们对法的理解仅限于国家的立法。
事实上,作为时间序列上的相对概念,中国古代法从未中断。只是我们的思考在不应该停止的地方中断了,从而导致中国法律传统与现实法律之间的断裂。中国传统法律展现为时间序列上的多重结构,清末修律这一政治决断,所带来的最大的断裂是“国法”层面的《大清律例》。只不过政治变迁有着清晰而统一的时间界标,而文化层面的“天理”“人情”的变迁缓慢而模糊,甚至因为其强大的惯性而延续至今。比如,民间习俗中的事实婚姻和法定婚姻成立的标准之间的冲突就能很好地反映文化层面的影响。当代中国法律规定婚姻成立的一个形式要件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而传统中国的婚姻遵循“六礼”的程序,一般而言,男女双方在完成“纳征”程序之后,也就是男方向女方家交了彩礼之后,双方的婚姻契约就生效了。此时,女方虽未过门,但是双方有了夫妻之名。这样一套缔结婚姻的程序和观念自周代形成以来,延续了近3000年,在民间根深蒂固。近几十年来,随着两性关系的松动,“六礼”程序被简化为男女双方订婚之后,默认双方可以同居,甚至默认彼此之间存在事实婚姻。然而,这种习俗与国家现行法律之间的界定标准并不一致。当下很多因婚恋关系引发的热门事件,背后都存在着这二者的冲突。类似的民情风俗与国家立法之间的张力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展现出传统对当下持续性的影响力。
另外,我们不可忽视汉语言文字的强大转译能力。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人类的每一种语言文字中都蕴含着特定的权力、规范、思维结构等。在近代西方法律概念转译成汉语的过程中,会选择某个汉语概念对译相关概念,汉语概念中蕴含的信息就构成了一个“前见”,或者说最终转译的法律概念是译者的中文视域与外文视域融合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规范不可避免地进入新概念中。举个例子,宪法中的“共和”概念,对译自英文中的“republic”。“republic”在西语中源自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政治学传统。但是近代早期的魏源、徐继畬等人对美国建国历史、对华盛顿的赞美、对美国共和政治体制的理解,都是从儒家“公天下”理念和“选贤与能”的角度展开的。汉语中的“共和”概念源自于周代的“共和行政”,一般认为是周厉王的残暴统治被推翻之后,国人推举了周定公和召穆公共同执政(一说为“共伯和”),是为“共和”。后来日本学者以汉语“共和”对译“republic”,也是看中了中国古典语境中“共和”所蕴含的“公天下”理想、“贤人政治”与“republic”的相通之处。其它如民法中的“合同”“债”,刑法中的“罪”“盗”等重要的基本概念,都是中国古代法律中固有的概念与欧陆相关法律概念融通互释的结果。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和规范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了当代中国法律体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下兴起的“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并不是要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地来建立起一套新的知识体系,而是要揭示中国当代法律概念体系中蕴含的传统渊源,或者通过诠释与转化,将部分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丰富到相关概念体系中。
4、您用心对待每一位学生,在指导学生学年论文时逐句批注、进行纸质修订。这种细致入微的关怀是否受您求学时的某位老师或某段经历影响?
这主要是受我导师李栋教授影响。李栋教授对学生特别认真负责,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最核心的是要肯在学生身上投入时间与精力。学生在学业上是否能够取得成就,一方面取决于学生是否勤奋努力,另一方面取决于指导老师的时间与精力的投入。李栋教授在指导学生论文的时候,会从最基础的开始教起,事无巨细、不厌其烦。如果学生的论文选了他不熟悉或者比较新的领域,他会跟学生一块学习,找文献、读材料。这样一方面降低学生论文选题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以向学生示范怎么发现问题,怎么写作。
我来法大之后,尽力延续了这一做法,不吝惜在学生身上花时间。例如,除了论文指导之外,在我每学期开设的《中国法律史》课程中,我都会逐一阅读、通过邮件回复和点评学生上交的上百份平时作业,指出其中的疏漏,有时还得查找资料验证。虽然这件事有些费时费力,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这样可以让学生感知到你在认真对待他们的作品。
5、您能谈一谈如何阅读吗?
阅读是一个很个性化的体验,如何阅读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你觉得好的、值得读的作品,其他人不一定感兴趣。每次学生让我推荐书单,我都会建议他们去寻找适合他们自己的书籍,并从中获得个性化的感悟。因此,我主要想从阅读的重要性和阅读的选择上向大家分享一些心得。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对于法学这类文科专业的学生而言,阅读是整个大学期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一个平庸的文科生和一个优秀的文科生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思维的深度与广度是文科专业毕业生之间最大的壁垒,也是个体最鲜明的特质。而这一特质的获得,离不开阅读,同时也必须由我们亲自去体悟,这是上课没法取代的。
其次,多读一些人文通识类作品。作为专业类院校,我们学校以法学专业为主。专业的法学教育是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的产物,但这种分化容易把法学教育强化成一种职业技术教育。在现代知识体系当中,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而又自洽的知识体系。如果我们只以考试为目标进行阅读,或者只读法律类书籍,可能会陷入一种“理性的牢笼”。而通识性的人文阅读,或许无法直接参与现实法律问题的讨论,也无法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与方案,但却是培养人、理解人类自身的关键。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人文通识类作品的阅读,去理解真、善、美,去陶冶、完备个体品格。